遥远的机杼声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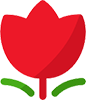 7
7

每次我翻阅《木兰辞》,“唧唧复唧唧,木兰当户织”的句子映入眼帘时,上世纪七十年代胶东乡村的冬夜光景,便会瞬间打开尘封的记忆,清晰地铺展在我的眼前。
那是被北风裹着寒气浸透的冬夜,铅灰色的云沉沉地压着屋脊,连村口的老榆树都缩着枝桠,像冻僵了的手臂。枯草碎屑被风卷着,在窗棂外打着旋儿,把窗户纸刮得“哗啦哗啦”响,街巷里,只有几声零星的犬吠,刚冒出头就被寒风噎了回去,天地间只剩下一片冷寂的黑。唯有我家的土坯房里,透出一星昏黄的煤油灯光,像冬夜里一点不肯熄灭的火种。屋里的土炕烧得暖烘烘的,堂屋里摆着一架黝黑的织布机,木质的机架被岁月磨得发亮,像浸过油的老檀木,机身上的木纹里,藏着数不清的寒来暑往。母亲坐在织布机前的板凳上,穿一件打了补丁的靛蓝土布褂子,正在织布。她是姐妹四人里最能干的一个,大舅远在沈阳的工厂里做工,难得回来一趟,家里的担子,母亲总要多扛几分。昏黄的灯光落在她脸上,映出眼角细密的皱纹,也映出她专注的眼神——双手执着枣木梭子,在纵横交错的经纱间轻快地穿梭,“咔嗒、咔嗒”,机杼声规律又清脆,穿透呼啸的风声。那机杼声穿越千年,与母亲织布的“咔嗒”声重叠,让人想起孟郊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”的咏叹,原来古今母亲的牵挂,都藏在针针线线里。就像鲁迅在《故乡》中写的,故乡的记忆总与那些“熟识的老物件”和“温暖的劳作场景”缠绕在一起,这架织布机,便是我记忆里最鲜活的印记。这声响,像极了明代沈周《暗纺词》里“车摇摇兮夜迢迢”的写照,只是母亲的夜织,不为“换米”果腹,只为让我们兄弟姐妹能穿上暖衣。“娘,歇会儿吧,明儿再织也赶趟。”我裹着薄棉被趴在炕沿上,看着母亲的影子被灯光投在土墙上,忽长忽短,像一株倔强生长的树。母亲头也没抬,手里的梭子依旧翻飞:“傻孩子,你们的棉裤还没着落,多织一寸,你们就暖和一分。”那时乡里有规矩,年前的布要赶在腊月廿三送灶神前织好,说是能讨个“岁岁安稳”的好彩头。
奶奶的纺车就摆在母亲的织布机旁,那架纺车早已辨不清原本的颜色。奶奶坐在蒲团上,佝偻着脊背,像一株被秋霜压弯的高粱。她的头发早已全白,用一根黑布条松松地绾在脑后,枯瘦的手指像老槐树的枝桠,握着纺锭轻轻摇动。油灯的光在她银白的发丝上跳跃,她的眼睛微微眯着,目光落在旋转的棉锭上,神情专注。棉絮在她手中渐渐抽成匀净的棉线,一圈圈缠在锭子上。这场景,让人想起茅盾《春蚕》中对农家劳作的细致描摹,更契合沈从文笔下“乡土间的劳作从不是苦役,而是藏着生活本真的温暖”的意境,奶奶的纺线,便是用最朴素的动作,编织着一家人的冬日暖意。“奶奶,你纺的线真匀溜。”二姐凑过去,伸手想摸那转动的锭子。奶奶抬手拍了拍她的手背,声音沙哑却温和:“慢工出细活,纺线和做人一样,得稳当。”纺好的线要先“浆线”,用米汤煮过,晾干了才好上机织布,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法子,说这样织出的布结实耐穿,还不容易起球。母亲常说,当年她和三个姨跟着姥娘学纺线织布,大舅在一旁看着,总说以后要在沈阳给她们买最时髦的洋布,这话,姥娘记了一辈子。
家里的自留地,就在村西的围子外,种着半亩棉花。秋阳高远的下午,母亲便带着大姐、二姐下地拾棉花。下午没有露水,棉花被太阳晒得蓬松。棉株不算高大,却缀满了雪白雪白的棉桃,炸开的棉絮像一团团蓬松的云,在蓝天下晃得人眼晕。母亲弯着腰,背脊像一张拉满的弓,手指在棉桃间翻飞,摘下的棉花放进腰间的粗布兜,沉甸甸的坠着。姐姐们跟在后面,小手里攥着两三朵棉花,脸蛋被秋阳晒得通红,像熟透的苹果,却笑得眉眼弯弯。这画面,颇有沈从文《边城》中“自然既长养人且教育人”的纯粹,田间的劳作与孩童的嬉闹,构成了乡村最动人的图景。“娘,你看这朵棉花,好大!”二姐举着一朵蓬松的棉絮,蹦蹦跳跳地跑到母亲身边。母亲直起身,擦了擦额角的汗,接过棉花看了看,嘴角弯起笑意:“攒着,给你小弟做新棉袄。”风拂过棉田,带着棉花的清甜气息,那气息里,藏着我们兄弟姐妹过冬的期盼。收完棉花,要摊在场上晒上几天,夜里再收起来防露水。村里,大人们凑在一起说收成、讲古,我们几个小的,就躺在一边数星星,听母亲说大舅在沈阳的新鲜事,说那里的工厂不像家里这样手工织布,却也一样离不了棉线的筋骨。
雪白的棉线,要织成布,再染上颜色,才算真正有了烟火气。织好的布匹被奶奶和母亲放进一口大铁锅里,锅里熬着蓼蓝的汁液,深蓝色的浆水冒着热气,咕嘟咕嘟地翻着泡,浓郁的草木气息弥漫了整个院子。那时村里没有染料铺,染布的蓼蓝都是自家种的,割了叶子沤在缸里,发酵后才能熬出蓝浆。原本素白的布,在染液里浸泡许久,捞出来时,已成了沉静的青色。染好的布要抻,奶奶和母亲一人拽着布的一头,双脚使劲蹬着地面,身子往后仰着,随着“嗨——嗨——”的号子声,用力将布抻得平整舒展。她们的额上渗着汗珠,脸上却带着笑意。“加把劲!抻得越平,衣裳越板正!”奶奶扯着嗓子喊,母亲应和着,号子声在空荡荡的院子里回荡,粗粝,却充满力量。抻好的布要晾在绳上,路过的婶子大娘见了,总要停下脚步夸两句:“你家的布染得真匀,看着就厚实!孩子们有福,身上的衣裳,亏得你娘俩手巧能干”她们的话,恰如其分地道出了母亲与奶奶的辛劳,也应了鲁迅所说“乡土的坚韧,都藏在这些日复一日的劳作里。”
裁衣的剪刀“咔嚓”作响,青色的布匹,变成了我们兄弟姐妹身上的新衣。做衣裳的日子,多半选在逢集的前一天,母亲会提前把针线笸箩收拾好,里面放着顶针、剪刀,还有几个备用的线。那时乡里的孩子,新衣裳都是“老大穿新,老二穿旧,老三穿打补丁”,可母亲总想着法子,给我们每个孩子都做一件新的,哪怕布料省了又省。二姨、三姨和四姨有时会来帮忙,四个姐妹围坐在炕沿上,飞针走线,说着家长里短,说着大舅寄来的信。“大哥来信说,沈阳的冬天比咱这儿冷多了,厂里发的棉袄都是大棉袄,比咱织的布还厚实。”二姨手里捏着针线,忽然开口。母亲抿嘴笑了笑,穿针引线的手没停:“他在外面不容易,咱在家把娃们照顾好,让他少操心。”四姨凑过来,摸了摸刚裁好的布角:“等开了春,咱也学着织点花格子布,给大哥寄去,让他也穿穿咱亲手织的布。”这话让奶奶听见了,她坐在一旁纳鞋底,接口道:“还是你们有心!”屋里的煤油灯,把四个姐妹的影子拉得老长,这场景,恰似鲍溶“蚕桑能几许,衣服常著新”的真实写照,母亲用一双巧手,在贫寒岁月里为我们织就了体面,也藏着沈从文笔下“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”的朴素幸福。棉裤棉袄,带着棉布的柔软,带着草木染的清香,穿在身上,暖暖的,心里更是甜的。
最盼的是过年。正月初三,天蒙蒙亮,雪花飘飘洒洒地落着,把屋顶、树梢都裹上了一层白,连土路都被盖得严严实实,踩上去“咯吱”作响。按照乡里的老规矩,初三是“走姥娘家”的日子,再大的雪也不能耽搁。我们兄弟姐妹,穿着青布新衣,踩着积雪,蹦蹦跳跳着去走姥娘家。雪地里的脚印,一串一串,看着就欢喜。进了姥娘家的门,掀开门帘,一股热气混着蒸年糕的香味扑面而来。姥娘正坐在蒲团上烧水,见了我们,布满皱纹的脸像一朵盛开的菊花。她拉着我们的手左看右看,目光落在我的棉裤上,忽然捂着嘴笑出了声:“哟,俺家来了个洋夷子!”
我低头一看,脸“腾”地一下红透了——棉裤腰耷拉下来一截,露出里面白花花的棉絮。我赶紧用手捂住,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母亲站在一旁,脸也红了,她上前轻轻拽了拽我的裤腰,又伸手理了理我的衣领,声音里带着点局促:“娘,都怪我,棉裤腰长了点。”姥娘拍了拍母亲的手,笑着摆摆手:“都是庄户人,谁家孩子的衣裳不露着棉花?等到了明年,孩子长高了,就好了!”
打那之后,母亲织布的时间更长了。冬夜里的机杼声,响得更勤,也更坚定。油灯的光晕里,她的身影愈发单薄,却挺得笔直,像村头那株白杨。她坐在织布机前,梭子穿梭得更快,机杼声更密。我知道,那是母亲的倔强——她不肯让孩子们在人前受委屈,她要让我们穿得体体面面,活得堂堂正正。就像孟郊笔下“意恐迟迟归”的慈母,她的爱,都藏在细密的经纬里;也如鲁迅在《热风》中所言“有一分热,发一分光”,母亲用她的坚韧,为我们撑起了一片温暖的天地。
后来,日子渐渐好起来,镇子上有了裁缝铺,集市上有了卖布的,又有了各色的成衣,家里的织布机和纺车,便渐渐被束之高阁,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尘。
姥爷姥娘去世的早,母亲中年时,眼睛就失明了,到了晚年,它总坐在炕上,摸索着翻出几块旧青布。那些布早已褪成了浅灰,边角磨出了柔软的毛边,却被她叠得方方正正,连一丝褶皱都没有。她枯瘦的手指,关节已经有些变形,却依旧轻柔地抚过布面的经纬纹路,一下,又一下,像是在抚摸襁褓里熟睡的婴孩。阳光透过窗棂,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,镀上一层柔和的金辉,她的眼睛虽然看不见什么,但嘴角噙着一抹淡淡的笑意,嘴里喃喃自语:“那时候夜里织布,总怕灯油费得多,就把灯芯捻得细细的,光暗得只能看清梭子的影子。”她顿了顿,指尖在一块布的补丁上轻轻摩挲,那补丁的针脚,比布面的纹路还要细密,“听着那‘咔嗒’声,就想着你们穿上新衣裳,蹦着跳着去姥娘家的模样,再累也不觉得了。”她抬起头,望向村西的方向,像是看见当年那片泛着棉絮的自留地,看见棉花地里的孩子。“人这一辈子啊,就像这织布,得一针一线地织,经是经,纬是纬,不能乱了章法,更不能辜负了手里的这团棉线。”她的声音轻得像一阵叹息,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。她说着,慢慢将布重新叠好,放起来,像是在珍藏一段永不褪色的时光。
再后来,父亲母亲和姨、姨夫们,也相继离开了这个世界。那架遥远的织布机,连同煤油灯的光晕、抻布的号子、雪地里的欢笑声,都被封存在记忆的深处。
每当我读到“木兰当户织”,读到“慈母手中线”,那些画面便会鲜活如初。那架织布机,织出的何止是布匹,更是一段贫寒却温暖的岁月,是母亲和奶奶如《凯风》所颂的勤劳与坚韧,是沈从文笔下“乡土中国最本真的温情”,也是鲁迅心中“永不磨灭的民间力量”。这些藏在典籍与记忆里的温暖,如同永不褪色的经纬,编织成了生命中最珍贵的底色,成为我一生都汲取不尽的精神养分。
【编者按】这篇散文,以《木兰辞》做引,打开了胶东乡村冬夜的温情记忆。母亲织布的机杼声、奶奶纺线的身影、拾棉花的欢闹、染布的烟火气,生活的细节鲜活可感,读来有乡土的质朴与真挚。母亲为儿女操劳的坚韧,晚年失明摩挲旧布的执念,皆藏着深沉的母爱与岁月的厚重,令人动容。编辑:穿越中的书生


